在架子上
管教所
塔那那利佛到期
畫廊:576 頁,29 美元
如果您購買我們網站上連結的書籍,《紐約時報》可能會從中賺取佣金 書店網站其費用支持獨立書店。
十月是黑人推理小說月,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塔那那利夫杜如此忙碌。 這位被稱為「黑色恐怖元老」的作家、編劇和教授正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沉沒之地》——其標題取自喬丹皮爾的突破電影《逃出絕命鎮》中的一個場景。 這門廣受歡迎的課程創建於2017 年,借鑒了她作為十幾本恐怖小說的作者和《恐怖小說》的執行製片人的經驗,透過黑人恐怖電影和小說的鏡頭探討了種族主義和生存。黑色恐怖,”關於這個主題的開創性紀錄片。
還有她的寫作。 隨著 WGA 罷工的解決,她和丈夫兼編劇搭檔史蒂文·巴恩斯 (Steven Barnes) 回到了布萊恩·富勒 (Bryan Fuller) 的《水晶湖》(Crystal Lake) 的編劇室。 備受期待的前傳 到「十三號星期五」系列。 她補充了她四月份的短篇小說集“許願池”,並在本月出版的選集“外面尖叫”中補充了一個新故事,該故事由皮爾策劃並介紹。 最重要的是,她即將出版今年的第二本書《感化院》,這是一本關於黑人和白人兒童在臭名昭著的佛羅裡達青少年懲教所所面臨的恐怖的成長小說。
喬·蒙蒂(Joe Monti)是西蒙與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新小說的編輯,當手稿第一次出現在他的辦公桌上時,他感到很驚訝。 他曾與杜談論過為史蒂芬·格雷厄姆·瓊斯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提供簡介,但不知道她正在寫一部新小說,這是她近十年來的第一部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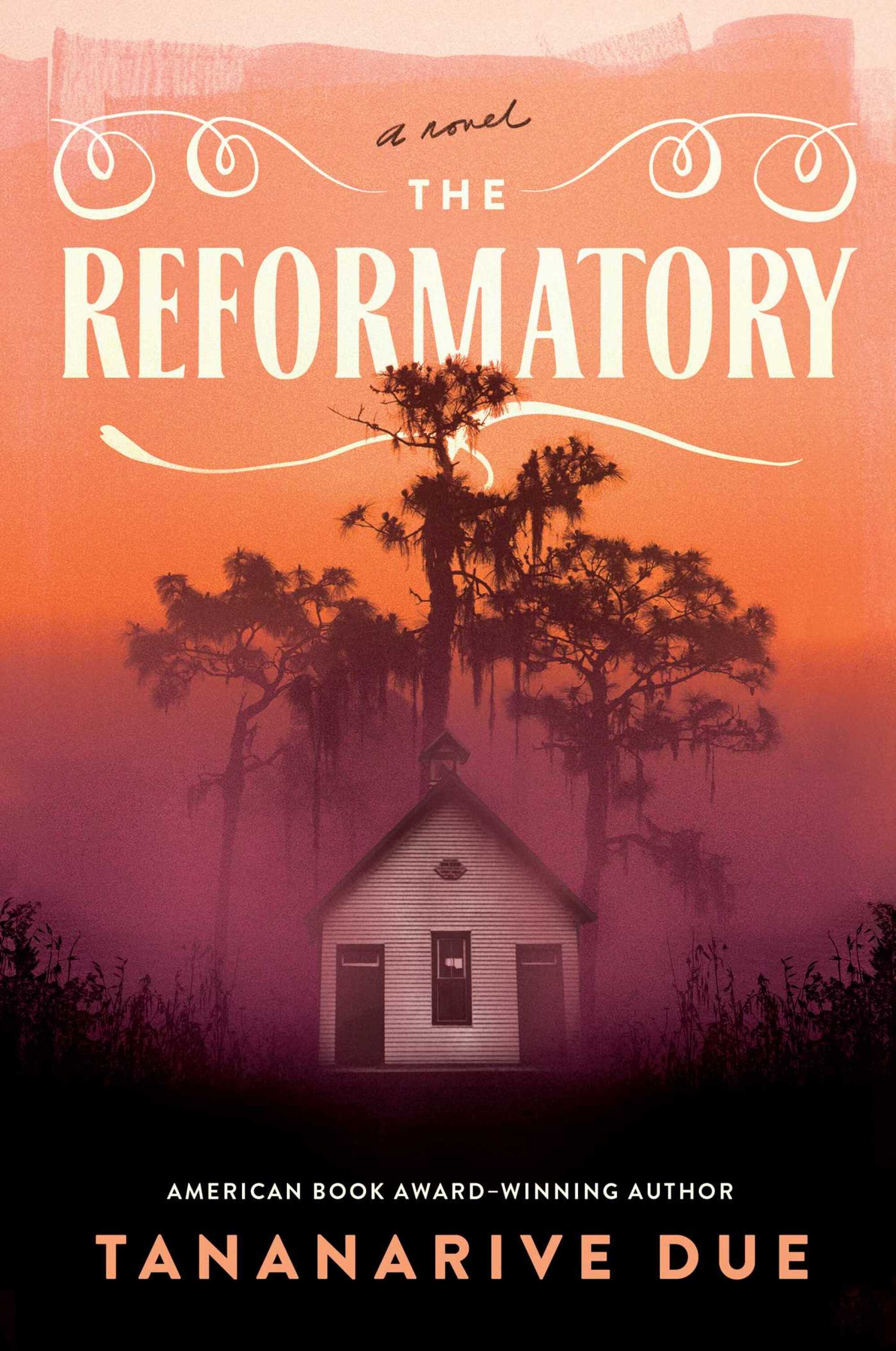
幾年來,蒙蒂一直在恐懼中尋找 BIPOC 的聲音。 「當然,我知道塔那那利佛是恐怖界中的佼佼者,並且幾年前就讀過《好房子》,」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但我又回到了那本書,讀了她早期的一本小說《我要保留的靈魂》,當我想透過回顧恐怖片最近的過去來出版恐怖片時,這有助於確定我在尋找什麼。”
雖然杜是黑色恐怖領域的先驅者,但她經常想到其他先驅者。 當她在Upland 的家庭辦公室透過Zoom 講述自己作為記者和作家的三十年時,一張海報在她肩上若隱若現:《家庭自由》的封面,這是她2003 年與母親帕特里夏·斯蒂芬斯‧杜(Patricia Stephens Due) 共同撰寫的回憶錄,一位民權運動家,於2012 年去世。(她的父親小約翰‧D‧杜伊(John D. Due Jr.),現年88 歲,是一名 民權律師。)
「我得到了父母堅定不移的支持,尤其是我的母親,」杜說。 「甚至在我出版之前,我媽媽就買了《作家市場》 [a guide to publishers and agents] 每年都作為生日禮物。 寫作對我母親來說很重要。”
但在西北大學讀本科期間,杜收到了關於什麼的複雜訊息。 種類 寫作很重要。 “雖然欣賞托妮·莫里森的《寵兒》讓我在寫作課上得到了讚揚,”她回憶道,她靠著鏡頭強調,“喜歡斯蒂芬·金卻讓我揚起了眉毛。”
在杜家卻並非如此。 “我的母親喜歡恐怖。 這就是我學會熱愛這一類型的方式。” 杜的父母很謙虛,但她從歷史書中了解到,他們是備受尊敬的人物。 他們對類型的認可應該已經足夠了——但她卻在努力寫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擔心如果我寫恐怖片,我不會受到尊重,」她說。 “我甚至不允許自己想像自己這樣做。”

「真正的恐懼是想到失去親人,」塔納那利夫·杜爾說。 “但在恐怖電影中,這就是我們的開始。”
(吉娜·費拉齊/洛杉磯時報)
1992 年,杜以《邁阿密先驅報》記者的身份接受了安妮·賴斯 (Anne Rice) 的採訪,這成為了一個重大轉折點。 賴斯曾被評論家指責浪費了她在吸血鬼主題上的才華,但這位暢銷書作家卻完美地捲土重來。 「賴斯說,『每個人都知道簡愛是誰…每個人都知道科學怪人的怪物是誰。 這些都是偉大、有力、英雄的形象,讓你能夠走出自我,真正談論那些改變你的問題。」賴斯接著描述了荷馬對他的聽眾的影響,被他的阿基里斯和特洛伊史詩故事所感動。 「這不僅僅是逃避,而且是一種可以提高你的逃避。 你回去感覺不一樣了。 這才是文學該做的事。”
九個月後,受到恐怖小說可以講述生活中最大挑戰這一觀念的啟發,杜完成了《介於兩者之間》,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男人的故事,他相信自己的瀕死經歷使他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幾乎摧毀了他的婚姻。 兩年後,她又推出了《我要守護的靈魂》(My Soul to Keep),講述了500 歲的非洲神仙大衛·沃爾德(David Wolde) 的故事,他對於保護自己的身份感到矛盾,因為這意味著要放棄他的人類家庭。 2009 年,《非洲不朽》系列的第三本書《血色殖民地》獲得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形象獎。
那時,Due 對各種讚譽並不陌生,但這次標誌著另一個轉折點。 「我母親告訴我,在20 世紀60 年代,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來建立比佛利山/好萊塢分會,因為他們當時了解代表權的重要性,這是民權鬥爭的另一個戰線。”
在杜的成長歲月裡,民權歷史是個永恆的話題。 「我的母親在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杜說。 「這就是我與她共同撰寫《家庭自由》的原因:不僅是為了保存我父母雙方的作品,而且對她來說很重要的是,為了保存其他無名活動家的作品,除非她講述,否則他們的故事將會被遺忘。 ”
杜對黑人歷史的崇敬——以及它給經歷過其恐怖的普通人造成的創傷——融入到了《感化所》中,這是一部懸疑的成長故事,講述了虛構的格雷斯敦12 歲的羅伯特「羅比」史蒂芬斯的成長故事。佛羅裡達州,因保護自己的妹妹免受一名白人青少年的不當挑釁而被送往臭名昭著的男孩拘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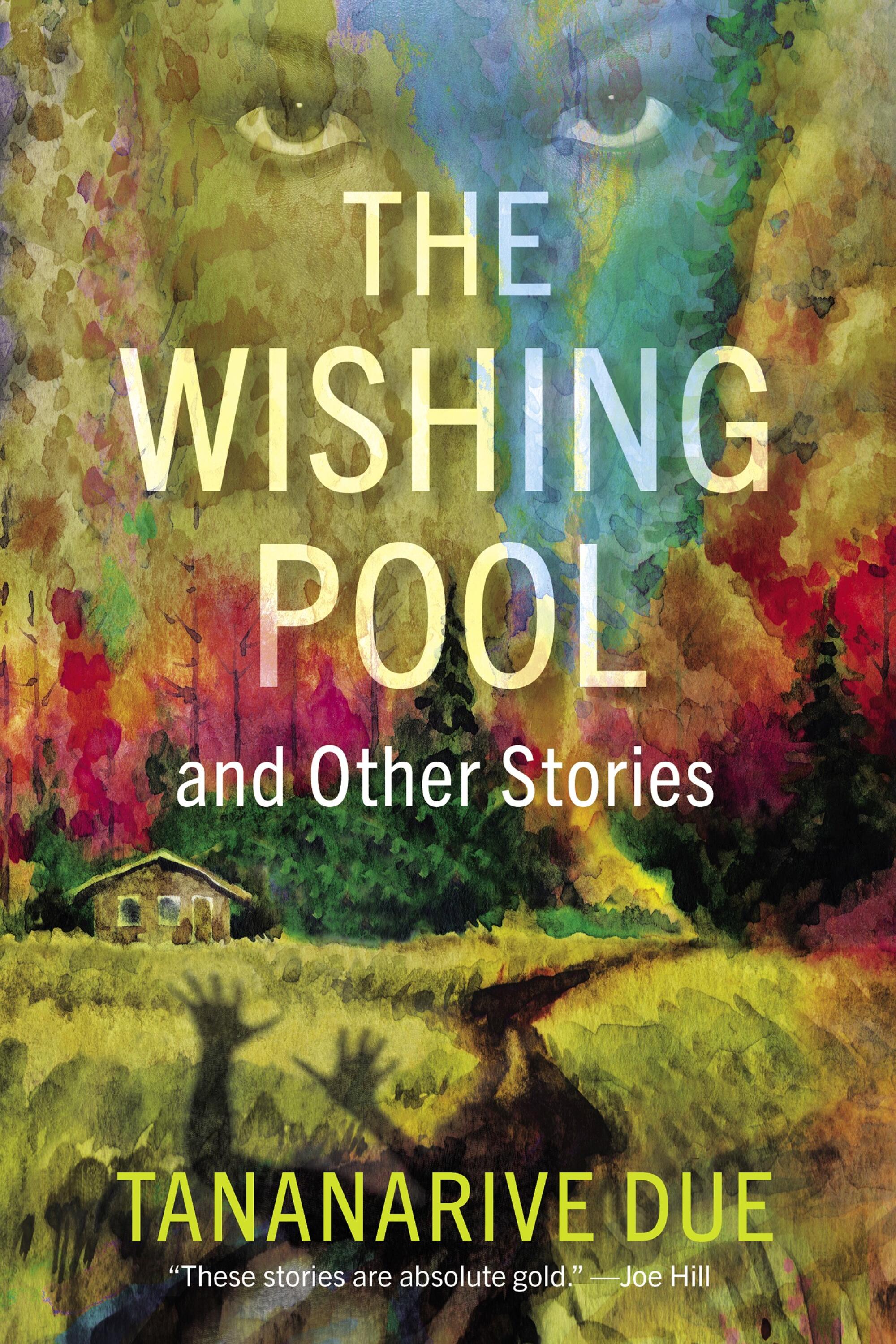
塔那那利夫‧杜伊的《許願池》
(阿卡什書籍)
靈感來自20 世紀30 年代佛羅裡達州聲名狼藉的多齊爾男子學校(Dozier School for Boys) 現實生活中失去親人的事件,這也是科爾森·懷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 普立茲獎獲獎小說《尼克男孩》(The Nickel Boys) 的基礎 杜在母親過世後不久開始寫這本小說。
“我們從來沒有機會談論發生過的事情”,杜伊對 1937 年在多齊爾學校去世的叔祖父說道。 在我們的談話中,她對損失和錯失機會的悲傷顯而易見。 「我有很多次希望能夠改變現實生活中的羅伯特‧史蒂芬斯的歷史,他那麼年輕就死在那個可怕的地方一個沒有標記的墳墓裡。 他們說他被刺傷了,但我相信其中一些記錄中有不誠實的地方。 這並不是太牽強,因為當你完全控制這樣的環境時,你就可以控制敘述。”
杜收回了這個敘述,將小說背景設定在她的叔公去世大約 13 年後。 管教所仍然是男孩們因輕微違法行為而遭到殘酷毆打的地方,而「haints」——死在惡毒典獄長手中的男孩的鬼魂——既引導又困擾著羅比。 然而,儘管這是一個種族主義恐怖故事,《感化院》也講述了羅比的姐姐格洛麗亞的英雄主義,她開始尋求解救曾經保護她免遭性侵犯的兄弟,並遭到殘酷的對待。為此受到懲罰。
推測因素很少——這一事實令蒙蒂感到驚訝。 「這種恐怖幾乎完全源於吉姆克勞時代的佛羅裡達州,」他說。 “這就是埃里森的《隱形人》的恐怖之處,這也是它如此引人入勝的原因。”
《感化所》和《許願池》中的幾個短篇故事也以格雷斯敦為背景,將佛羅裡達州的種族歷史和杜自己的家族傳奇的許多線索編織在一起,為恐怖迷創造了一個像斯蒂芬·金的城堡岩一樣強大的背景。 但杜伊對格雷斯敦的靈感來自威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儘管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我希望我的縣成為一個神奇的事情發生的地方,尤其是當它們與黑人兒童有關時。” 雖然格雷斯敦確實有魔力,但它也是角色處理和治癒創傷的地方。
在《逃出絕命鎮》和《黑色恐怖》紀錄片之後,Due 開始將她母親對恐怖的熱愛與她 20 世紀 60 年代的創傷聯繫起來。 「我母親被警察發射催淚瓦斯,由於眼睛受傷,她不得不戴上墨鏡,」她回憶道。 「在另一起事件中,她姐姐的腹部被踢。 我姑姑對美國的幻想破滅了,她移民到了加納,每次試圖返回美國時,她都得了蕁麻疹。”
杜想知道恐怖是否對她的母親來說是一種安慰。 「當你真正經歷過創傷時,恐怖可能會給你帶來一種奇怪的安慰,」她說,「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一本書或一部電影是對你的情緒和恐懼的驗證。 你意識到你在電影中感受到的恐懼與現實生活中的恐懼是一樣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背景下。 越是幻想的背景,它就越能與你所遭受的實際創傷分開。 我必須相信我的母親發現它以這種方式治癒。 不知道她是否會同意。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也遭受了自己的創傷,其中最大的就是失去了我的母親,我現在明白了。”
看著父親的衰老和衰弱,杜現在與妹妹住在亞特蘭大,也讓杜意識到恐怖可以如何舒緩情緒。 「觀看有關照顧的恐怖電影讓我感到安慰,因為真正的恐怖是看到你所愛的人無法再像以前那樣照顧自己,」她說。 「真正的恐懼是想到失去親人。 但在恐怖電影中,這就是我們的開始。”
她的眼睛閃閃發光,補充道:“然後你再加上一個惡魔,恐怖就可以解決了。”
伍茲的《內城布魯斯》是《夏洛特正義》系列的第一部,最近被《時代》雜誌評為有史以來 100 本最佳懸疑/驚悚小說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