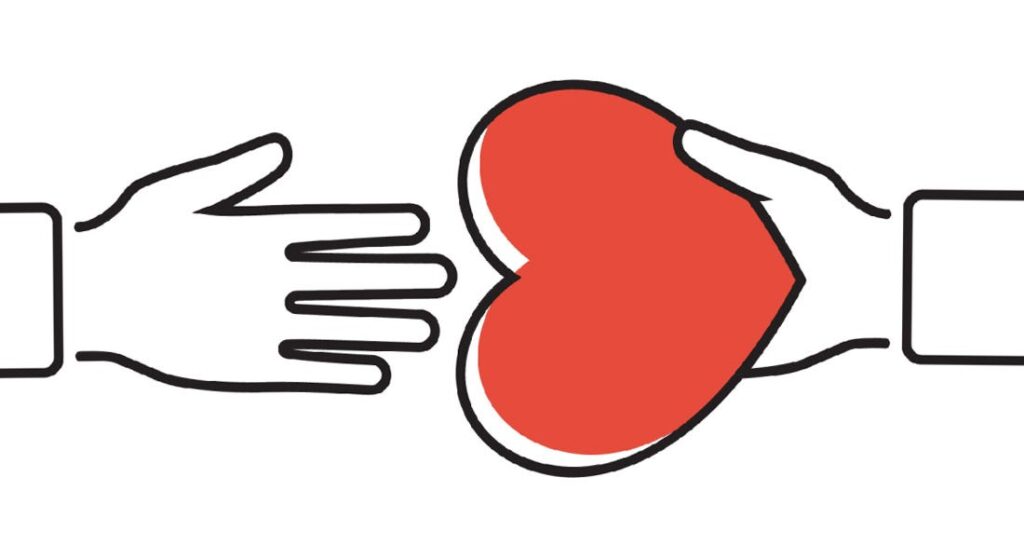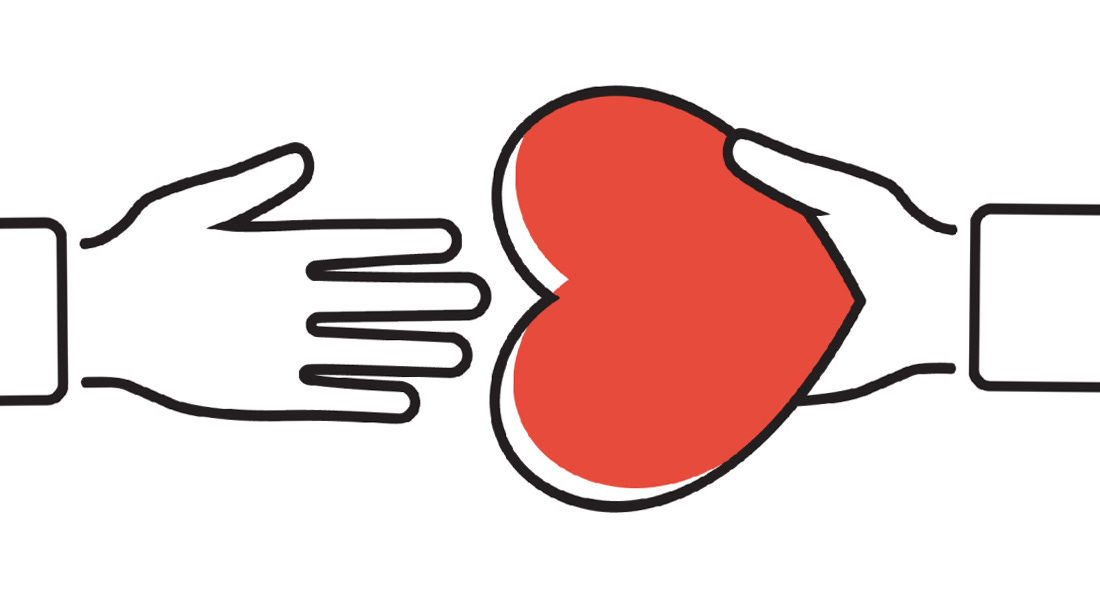
雷和丹是兄弟,也是我常去的愛爾蘭酒吧的調酒師。 儘管他們共同擁有這家酒吧並一起管理酒吧,但他們已經很多年沒有互相說過話了。 眾所周知,他們的不和始於雷與妻子分手並與丹的漂亮女友有染。 她隨後離開丹嫁給雷。 酒吧的常客每天晚上都會感受到緊張的氣氛。 在酒吧里一個忙碌的夜晚,一位年長的顧客試圖讓自己的聲音在人群中被聽到,他對兄弟之間的團隊合作進行了評論。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是怎麼做到的,”他說道。 “你們合作得真誠懇!”
丹暫時從自己的任務中分心,出人意料地嚴肅地回答道:“這不是‘誠意’。” 它是真實的。”
酒吧里瞬間鴉雀無聲,對丹的評論感到困惑。 然而,他說的卻是事實。 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都知道,兄弟倆的合作不僅僅是為了面子和顯示團結; 他們的酒吧備受推崇,儘管關係複雜,但他們都在真誠地履行自己的商業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真誠”意味著有意識地努力表現出誠實或開放,通常是出於希望以某種方式被感知的願望。 “真實”或 真正的c 意味著忠於自己和自己的價值觀,尤其是在面對挑戰和障礙時。
在他的經典中 真誠與真實y,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特里林談到了其中的區別。 他說,近代以前,真誠是指以外表表達內心情感,一般符合社會規範和期望。 現代文化已經從重視一種公開的、墨守成規的真誠轉向更加內省、有時甚至是叛逆的真實性。 “曾經被認為構成文化結構的許多東西現在看來已經無關緊要……相反,文化傳統上譴責和試圖排除的許多東西由於其真實性而被賦予了相當大的道德權威, [for example, antagonism, disorder, violence, unreason]”。
真誠就是有禮貌; 真實性更引人注目。 它使我們的關係變得更有意義,並區分真實與膚淺。 我們的工作不能膚淺。
在尋求脫穎而出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最終會融入別人,符合別人的期望。 在酒吧的緊張氣氛中,雷和丹沒有達到顧客的期望。 他們的敵意很強烈,但他們對酒吧的承諾更加堅定。
這個小插曲成為一個重要的提醒:對手可以是好的盟友,衝突是增長的催化劑。 我們應該將“盟友”視為動詞。 我們 能 挽著手走 沒有 眼對眼。 和解不僅僅是兄弟之愛。
筆記和閱讀
真誠與真實 ——萊昂內爾·特里林 (1973)。 [Cf. Genuine Pretending: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Zhuangzi – Hans-Georg Moeller, Paul J. D’Ambrosio (2017): New insights into early Daoist thought (4th c. BCE) and a paradigm of “genuine pretending” as an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 and Confucian! – notions of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While Trilling doesn’t speak of Daoism (as far as I know), the mid-20th century saw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Eastern thought among Western intellectuals that continues today. * See below]
和解:治愈內在小孩 – 一行禪師,越南佛教禪師、世界著名精神導師、和平活動家。 特別參見第一部分第七章“和解”(2006 年 – Kindle 版可用)。
在復仇與寬恕之間—— 瑪莎·米諾,哈佛法學院(1999 年)。 通過“引人入勝”的國際案例研究,米諾將正義的要求與治癒的需要聯繫起來,探索我們復仇和救贖的能力。
出路:如何克服有毒極化 – Peter T. Coleman,社會心理學家,哥倫比亞(2021 年)。 擺脫根深蒂固的敵對行動,包括案例研究。
盟國 – 波士頓評論論壇(24 篇文章) – 秋季(2019 年),尤其是 179-187。
[ * Daoist philosophy, as found in the Zhuangzi, often challenges rigid dichotomies still prevalent in Western thought. A famous story points out the problem: “Once upon a time, I, Zhuangzi, dreamt I was a butterfly, fluttering hither and thither,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 butterfly. I was conscious only of my happiness as a butterfly, unaware that I was Zhuangzi. Soon I awoke, and there I was, veritably myself again. Now I do not know whether I was then a man dreaming I was a butterfly or whether I am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I am a man.” – Boundaries are blurred between “real” and “illusion,” daily life and dreaming.]